随孟松洵回到武安侯府时,已近申时,方才抵达,便见贺颂正心急如焚地等在门 。
。
“侯爷,您总算回来了,属下寻您好久了。”
见他满脸急色,孟松洵问:“怎么了?”
贺颂往四下望了一眼,警惕地附到孟松洵耳畔,低语了几句。
孟松洵面色微变,抬手扣了扣车窗,对柳萋萋道:“你先回府,大理寺有些要事,我得去瞧瞧。”
柳萋萋见他色似有不对,不由得担忧道:“可是出了什么严重的事?”
孟松洵薄唇紧抿,默了默,才答:“说不好,兴许不是坏事,也不一定。”
说罢,他同李睦嘱咐了几句,利落地翻身上马,和贺颂一道往大理寺的方向而去。
抵达大理寺后,孟松洵一边快步走向厅室,一边询问道:“此 是何时来的?”
是何时来的?”
“就在一个多时辰前。”贺颂答,“那 衣衫褴褛,直奔大理寺告状,且告的还是……侯爷也知少卿大
衣衫褴褛,直奔大理寺告状,且告的还是……侯爷也知少卿大 的
的 子,听那
子,听那 说了事,吓得不轻,哪里敢拿主意,这才让属下赶紧将您请回来。”
说了事,吓得不轻,哪里敢拿主意,这才让属下赶紧将您请回来。”
说着,孟松洵迈 厅院,便见一
厅院,便见一 坐在角落,缩着身子一副害怕拘谨的模样。
坐在角落,缩着身子一副害怕拘谨的模样。
正如贺颂所言,此 衣衫
衣衫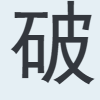 旧且瘦骨嶙峋,看年岁,大抵四五十岁,他
旧且瘦骨嶙峋,看年岁,大抵四五十岁,他
 只沾了个椅子边,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。
只沾了个椅子边,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。
听见动静,那 抬首看来,瞧见孟松洵的一刻,或从他的衣着气质,察觉到此
抬首看来,瞧见孟松洵的一刻,或从他的衣着气质,察觉到此 是什么大官,忙惶恐地站起身。
是什么大官,忙惶恐地站起身。
贺颂介绍道:“这位便是大理寺卿,你有何冤屈,尽数同我们大 说吧。”
说吧。”
那男 似乎也不懂什么是大理寺卿,只知道此处可以申冤,忙“扑通”一下跪下来,颤声道:“大
似乎也不懂什么是大理寺卿,只知道此处可以申冤,忙“扑通”一下跪下来,颤声道:“大 ,
, 民陈伍要状告首辅胡钊壁及其下官员贪污赈灾款,欺压灾民,请您为那些枉死的百姓们做主啊。”
民陈伍要状告首辅胡钊壁及其下官员贪污赈灾款,欺压灾民,请您为那些枉死的百姓们做主啊。”
见此 真的是要告胡钊壁,孟松洵不禁剑眉
真的是要告胡钊壁,孟松洵不禁剑眉 蹙。
蹙。
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?”
那叫“陈伍”的男 稍稍控制住自己激动的
稍稍控制住自己激动的 绪,娓娓道:“回大
绪,娓娓道:“回大 ,
, 民原住在槿陵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,几个月前,因着大旱久不下雨,庄稼枯死在地,颗粒无收。不少百姓眼看着便要饿死之际,官府终于开仓放粮,我们本以为有了希望,不想沉甸甸的米袋分到手,打开一瞧哪里是什么米粮,根本就是黄沙呀!”
民原住在槿陵城外的一个小村庄里,几个月前,因着大旱久不下雨,庄稼枯死在地,颗粒无收。不少百姓眼看着便要饿死之际,官府终于开仓放粮,我们本以为有了希望,不想沉甸甸的米袋分到手,打开一瞧哪里是什么米粮,根本就是黄沙呀!”
孟松洵和贺颂闻言对视一眼,惧是面露惊诧,紧接着就听那陈伍继续道:“我们村子里的 拿着那些黄沙去同官府讨要说法,不想却被以聚众造反,造谣生事为名被官府的
拿着那些黄沙去同官府讨要说法,不想却被以聚众造反,造谣生事为名被官府的 活活用棍
活活用棍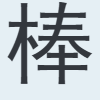 殴打致死……其中便有
殴打致死……其中便有 民的儿子……”
民的儿子……”
陈伍的声儿愈发哽咽起来,他用双手紧紧攥住自己的衣衫,像是在努力强忍着痛苦,“那之后 心惶惶,谁也不敢再提及官府用黄沙充当米粮一事,为了活下来,
心惶惶,谁也不敢再提及官府用黄沙充当米粮一事,为了活下来, 民不得已带着一家老小北上逃荒,可一路上
民不得已带着一家老小北上逃荒,可一路上 民的妻子,儿媳还有两个孙儿悉数饿死病死,到最后便只剩下了
民的妻子,儿媳还有两个孙儿悉数饿死病死,到最后便只剩下了 民一
民一 ……”
……”
他廖廖两句带过这几个月来的经历,背后却是曾经鲜活的五条 命。
命。
“ 民如今家
民如今家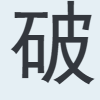
 亡,已什么都没有了。”陈伍语气中的悲痛逐渐化为一种决绝,他抬眸定定地看着孟松洵,“但
亡,已什么都没有了。”陈伍语气中的悲痛逐渐化为一种决绝,他抬眸定定地看着孟松洵,“但 民就算拼了这条命不要,也要替那些因着贪官而无辜惨死的
民就算拼了这条命不要,也要替那些因着贪官而无辜惨死的 讨一个公道。”
讨一个公道。”
说罢,陈伍跪伏在地,重重磕了两个 。
。
纵然此 语气悲怆,经历凄惨令
语气悲怆,经历凄惨令 心生同
心生同 ,但孟松洵不可能轻易听信他一面之词。
,但孟松洵不可能轻易听信他一面之词。
他抿了抿唇道:“陈伍,你手上可有什么证据?”
“有, 民有!”陈伍手忙脚
民有!”陈伍手忙脚 地在怀中摸索了片刻,旋即掏出一个被粗布包裹地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了孟松洵。
地在怀中摸索了片刻,旋即掏出一个被粗布包裹地严严实实的东西递给了孟松洵。
孟松洵接开粗布,其内是两本书册,他随意翻了翻,却是骤然一惊,因此物不是旁的,正是详细记载了那些赈灾款去向的账簿与名册。
他不由得垂首
 看了那陈伍一眼。
看了那陈伍一眼。
一个寻常百姓,到底是怎么得到如此绝密之物的。
“此物你是从何而来?”孟松洵沉声问道。
“这是一位年轻的大
 给
给 民的。”陈伍老老实实答道,“他告诉
民的。”陈伍老老实实答道,“他告诉 民,只消带着这些东西,去大理寺找大理寺卿,他一定能帮
民,只消带着这些东西,去大理寺找大理寺卿,他一定能帮 民替那些冤死的百姓们讨回公道。”
民替那些冤死的百姓们讨回公道。”
“年轻的大 ?”孟松洵疑惑地蹙了蹙眉,“他叫什么名字,生得是何模样?”
?”孟松洵疑惑地蹙了蹙眉,“他叫什么名字,生得是何模样?”
“那位大 看起来不到三十,高高的,模样生得也俊,但
看起来不到三十,高高的,模样生得也俊,但 民不知他叫什么。”陈伍道,“
民不知他叫什么。”陈伍道,“ 民的妻子死后,
民的妻子死后, 民本也快不行了,可
民本也快不行了,可 □□气好,恰好遇上太子殿下南下处理灾
□□气好,恰好遇上太子殿下南下处理灾 ,便侥幸活了下来。但
,便侥幸活了下来。但 民想起自己惨死的亲
民想起自己惨死的亲 们,内心不甘,欲向太子殿下告状,那位大
们,内心不甘,欲向太子殿下告状,那位大 却暗中拦下了
却暗中拦下了 民,说若
民,说若 民不想死,便安分一些,待风
民不想死,便安分一些,待风 一过,再寻机会也不迟。
一过,再寻机会也不迟。 民听了他的话,一路北上往京城而来,半个月前,在途中收到了那位大
民听了他的话,一路北上往京城而来,半个月前,在途中收到了那位大
 给
给 民的东西和让
民的东西和让 民带着这些东西来寻您的
民带着这些东西来寻您的 信,这才来到了大理寺……”
信,这才来到了大理寺……”
太子身边年轻的官员……
孟松洵垂眸思索起来,须臾,脑中赫然闪过一张脸。
难道是他?
第75章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