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是一个忍辱负重的纤夫,肩膀上被勒出一道道的血印。
长城啊,露天的军事博物馆,良心的试金石,无字的纪念碑,停摆的钟——指针永远指向昨天。一个民族漫长的回忆录。
今天,我也像许多消失的英雄一样,在长城前勒马,在长城下放牧。
车往回开,继续寻找去雾灵山的路。雾灵山屹立于北京市密云县与河北省的 界处。清代圣祖仁皇帝曾赋诗《晓发古北
界处。清代圣祖仁皇帝曾赋诗《晓发古北 望雾灵山》:“流吹凌晨发,长旗出塞分。运峰犹见月,古木半笼云。地迥疏
望雾灵山》:“流吹凌晨发,长旗出塞分。运峰犹见月,古木半笼云。地迥疏 迹,山回簇马群。观风当夏景,涧
迹,山回簇马群。观风当夏景,涧 自含薰。”只是如今的雾灵山已作为一自然保护的森林公园。我们的轿车可比大清皇帝的马队快多了,没一会工夫就抵达了山脚下的曹家路村。
自含薰。”只是如今的雾灵山已作为一自然保护的森林公园。我们的轿车可比大清皇帝的马队快多了,没一会工夫就抵达了山脚下的曹家路村。
俗话说靠山吃山,曹家路村沾了雾灵山的光,靠旅游经济发展起来了。农民们纷纷把自家的四合院改造成民俗旅馆,供远道而来的游客食宿。我们几个 有幸在烧得滚烫的大炕上过了一夜,连梦都散发出烤玉米的香味。
有幸在烧得滚烫的大炕上过了一夜,连梦都散发出烤玉米的香味。
第二天早起,在村子周围逛了一圈,发现不少处古长城的遗迹。有时一抬 ,看见迎面的山
,看见迎面的山 上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穹窿顶的敌楼,像戴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帽子。由于绵延的城墙湮没了,这悬崖上的楼便显得尤其突兀——让
上孤零零地耸立着一座穹窿顶的敌楼,像戴着一顶威风凛凛的帽子。由于绵延的城墙湮没了,这悬崖上的楼便显得尤其突兀——让 猜测当年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(不会是天兵天将吧?)其实这并不怪。长城在密云全县左盘右屈,沿线共有敌楼、战台666座,几乎扼守了所有的
猜测当年战士是怎么爬上去的(不会是天兵天将吧?)其实这并不怪。长城在密云全县左盘右屈,沿线共有敌楼、战台666座,几乎扼守了所有的 通要冲和险要山
通要冲和险要山 。只可惜,由于修路、盖房子,大段大段城墙被拆毁了,或者留下醒目的路
。只可惜,由于修路、盖房子,大段大段城墙被拆毁了,或者留下醒目的路 。我多次目睹农民家的屋脊后面露出半裁城墙的横切面,抑或在墙根下盖起的猪圈——长城就这样被糟踏着。好在它早已宠辱皆忘。
。我多次目睹农民家的屋脊后面露出半裁城墙的横切面,抑或在墙根下盖起的猪圈——长城就这样被糟踏着。好在它早已宠辱皆忘。
向村民打听,才知道曹家路原本是长城一道关隘的名称。那时候关隘的里侧一般都筑有用于屯兵养马、聚 存粮、驻扎后援部队的戍堡——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曹家路村。村子的外围原本有城墙环卫的,解放后拆掉了。有路牌的村
存粮、驻扎后援部队的戍堡——也就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曹家路村。村子的外围原本有城墙环卫的,解放后拆掉了。有路牌的村 ,原本是城门的位置。可见曹家路村的前身是戍边的兵营,说不清从何时起转为民用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是明清时边防军
,原本是城门的位置。可见曹家路村的前身是戍边的兵营,说不清从何时起转为民用的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:相当一部分土著居民是明清时边防军 的后裔。了解到这点之后,我果然察觉路遇的村民眉宇间都不乏英武之气——哪怕是一个拎着铲子拾粪的羊倌。
的后裔。了解到这点之后,我果然察觉路遇的村民眉宇间都不乏英武之气——哪怕是一个拎着铲子拾粪的羊倌。
历代的长城,也养活了不少 啊。沿着长城的藤蔓,像结果子一样,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村落。曹家路村,在我眼中是一个香
啊。沿着长城的藤蔓,像结果子一样,产生了大大小小的村落。曹家路村,在我眼中是一个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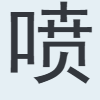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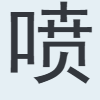 的大南瓜。我居然在这大南瓜里美美地睡了一觉。连梦中流的涎水都是甜丝丝的。
的大南瓜。我居然在这大南瓜里美美地睡了一觉。连梦中流的涎水都是甜丝丝的。
勒马长城,枕戈待旦抑或解甲归田,是两种不同的诗意。这也构成了战争与和平的区别。在曹家路村,我看见了战争与和平的分水岭:一边是烽火楼台的长城,一边是炊烟袅袅的民居。
跟早已成为旅游热点的居庸关、司马台相比,古北 更富有一种沧桑的美。这恐怕因为它缺乏修缮、多有残损,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孤儿或弃
更富有一种沧桑的美。这恐怕因为它缺乏修缮、多有残损,看上去像是历史的孤儿或弃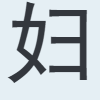 ,蓬
,蓬 垢面。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:古北
垢面。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:古北 一带的长城是不收门票的,如同尚未被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,有时候突然冒出来,吓你一跳——一眨眼又找不见了。而居庸关呀什么的,已被驯化为撩拨游客雅兴的宠物,有点假,有点做作,让
一带的长城是不收门票的,如同尚未被圈养起来的野生动物,有时候突然冒出来,吓你一跳——一眨眼又找不见了。而居庸关呀什么的,已被驯化为撩拨游客雅兴的宠物,有点假,有点做作,让 怀疑是
怀疑是 心搭设的电影布景。
心搭设的电影布景。
当然,我并不是说居庸关有什么不好,我说的是气氛——因为 流如织,快变成露天的大杂院了。至于居庸关本身,实在是太了不起了!
流如织,快变成露天的大杂院了。至于居庸关本身,实在是太了不起了!
所谓的居庸关,纵 四十里,俗称关沟——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。古北
四十里,俗称关沟——在我眼中就像是群山夹峙间的一条漫长的胡同。古北 倚托着燕山山脉,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——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。自南
倚托着燕山山脉,居庸关则属于太行山系——是其八条自然通道之一。自南 (又叫夏
(又叫夏 或下
或下 )
) 山,北
山,北 就是八达岭。共有四重关隘:南
就是八达岭。共有四重关隘:南 关城、居庸关长城、上关关城、北门锁钥关城。早在《后汉书》里就有记载:建武十五年徒雁门、代、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关以东。《唐书》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(即居庸关)。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:《淮南子》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,《金史》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、蜀之剑门相提并论,开容其险峻。至于今天,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,俗话说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,已主要指爬八达岭。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“劳模”的意味,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
关城、居庸关长城、上关关城、北门锁钥关城。早在《后汉书》里就有记载:建武十五年徒雁门、代、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关以东。《唐书》里也提及幽州昌平西北三十五里有纳欣关(即居庸关)。它很久以前就已是一座明星式的关城:《淮南子》称之为天下九塞之一,《金史》也把中都的居庸与秦之淆函、蜀之剑门相提并论,开容其险峻。至于今天,则把居庸关的八达岭树立为北京长城的表率,俗话说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,已主要指爬八达岭。于是八达岭长城带有“劳模”的意味,每天都有数不清的游 吭哧吭哧地爬呀爬,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。我真担心: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。好在它也受到最舍得下本钱的维修——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,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。既然存此疑虑,我索
吭哧吭哧地爬呀爬,为了到山顶满足一番虚荣心。我真担心:总有一天长城会被爬塌的。好在它也受到最舍得下本钱的维修——我不知道八达岭的城砖有多少块是旧有的,又有多少块是后来添加的。既然存此疑虑,我索 将其视为赝品。
将其视为赝品。
居庸关几度成为历史的休止符:金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,元兵是从这里打进来的(后来也是由这里退场的),李自成是从这里打进来的……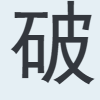 关之后,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
关之后,北京城自然也像核桃仁一样 露出来了,任
露出来了,任 取舍。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,专门有
取舍。但也不能完全责怪居庸关的失职,专门有 为其辩护:“此城非不高,兵非不多,粮非不足也;国法不行,而
为其辩护:“此城非不高,兵非不多,粮非不足也;国法不行,而 心去也。”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,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
心去也。”恐怕正因为受此害影响,康熙才把长城视为无关痛痒的赘 。
。
在居庸关通往北京城的途中,有一尊李自成快马加鞭的纪念塑像。(后 树立的)。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,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。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,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——成为一尊令
树立的)。他正如探囊取物般直奔紫禁城的太和殿而去,渴望在龙椅上歇歇脚。可是他为什么忽然勒住了马,永远地停留在过程之中——成为一尊令 慨叹不已的雕塑。打江山很容易,坐江山很难,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
慨叹不已的雕塑。打江山很容易,坐江山很难,于是像李闯王这样的英雄 物,也只能勒马长城了——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。每逢看见这尊铜像,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:李闯王,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,在关键的时候,勒住了自己的马?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,一览众山小?或许,不是你勒马,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疆绳给勒住了,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。这就是历史: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!
物,也只能勒马长城了——也只能留下无法弥补的缺憾。每逢看见这尊铜像,我总要想恨铁不成钢:李闯王,你为什么偏偏要在冲刺的时候,在关键的时候,勒住了自己的马?你为什么不更上一层楼,一览众山小?或许,不是你勒马,而是你本身被一根看不见的疆绳给勒住了,你被小农意识所制约。这就是历史:差一点点火候都不行!
在这一点上,当代伟 **则要高明得多。他1949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,特意做了个报告,大意为“我们不能学李自成”以及“要防止糖衣炮弹”之类。他在庆祝攻克国民党老巢南京的胜利时,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
**则要高明得多。他1949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,特意做了个报告,大意为“我们不能学李自成”以及“要防止糖衣炮弹”之类。他在庆祝攻克国民党老巢南京的胜利时,写下了这样的诗句: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
以“造反派”的身份攻克帝都,并且还 死了皇帝——这就是李自成。他不仅做了梁山好汉宋江所不敢做的梦(“杀了鸟皇帝”),而且他那种“擒贼要擒王”的勇气与魄力,恐怕连后来的洪秀全也要自叹弗如。难怪当时有迂腐的儒生感叹:“这
死了皇帝——这就是李自成。他不仅做了梁山好汉宋江所不敢做的梦(“杀了鸟皇帝”),而且他那种“擒贼要擒王”的勇气与魄力,恐怕连后来的洪秀全也要自叹弗如。难怪当时有迂腐的儒生感叹:“这 为千古历来流寇所未有。他的猖獗,除是唐末五代之间黄巢一个
为千古历来流寇所未有。他的猖獗,除是唐末五代之间黄巢一个 可以比得他住,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。”
可以比得他住,余外就没有与他比的了。”
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二月,揭竿而起的李闯王自西安发兵,经过山西大同,直 居庸关。目标很明确:“今大兵既兴,志在与朱明共争天下,若
居庸关。目标很明确:“今大兵既兴,志在与朱明共争天下,若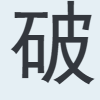 北京,则国皆为我有关。”过关斩将之后,于三月十六
北京,则国皆为我有关。”过关斩将之后,于三月十六 围困了笈笈可危的北京城。三月十八
围困了笈笈可危的北京城。三月十八 傍晚攻克广宁门(今广安门),导致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吊死在一棵树上——他自尽前还在推卸责任:“君非亡国之君,臣是亡国之臣。”第二天早晨,李自成率领大部队通过大明门(即**),像梦游一样进
傍晚攻克广宁门(今广安门),导致山穷水尽的崇祯皇帝吊死在一棵树上——他自尽前还在推卸责任:“君非亡国之君,臣是亡国之臣。”第二天早晨,李自成率领大部队通过大明门(即**),像梦游一样进 紫禁城。据说
紫禁城。据说 戴白色毡笠、身穿蓝布箭衣、骑着乌龙马的李闯王,张弓搭箭,轻而易举地
戴白色毡笠、身穿蓝布箭衣、骑着乌龙马的李闯王,张弓搭箭,轻而易举地 中了城楼上的门匾——以这礼仪
中了城楼上的门匾——以这礼仪 的动作来象征一个农民对一个王朝的致命一击!这一箭戳穿了泱泱大朝的脊梁骨,以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话。可惜呀可惜,明代不遗余力地修筑了二百余年的长城,简直像纸老虎一样,在瞬间就垮台了。长城是它的墓志铭。
的动作来象征一个农民对一个王朝的致命一击!这一箭戳穿了泱泱大朝的脊梁骨,以及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话。可惜呀可惜,明代不遗余力地修筑了二百余年的长城,简直像纸老虎一样,在瞬间就垮台了。长城是它的墓志铭。
李自成骑马跨越长城之间,想些什么?已不可知了。正如自居庸关至北京城途中的那尊闯王塑像——表 模糊、高
模糊、高 莫测。想当皇帝是肯定的,想搜罗点
莫测。想当皇帝是肯定的,想搜罗点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