粮铜也是可以理解的,错只错在他还想到了衣锦还乡(典型的中国 发户的理想)——荣宗耀祖,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。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。李自成认为“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”,可见他并不
发户的理想)——荣宗耀祖,并且让街坊四邻羡慕。这一点是有史料可查的。李自成认为“十个燕京也比不上一个西安”,可见他并不 愿在北京安家落户(“北京不是我的家,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”?)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、饮马、歇脚、饱餐一顿之后,还是要打道回府。当然,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。所以他特设“比饷镇抚司”,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、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,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——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。如此地易于满足——这样的胸襟,确实显得有点小了。
愿在北京安家落户(“北京不是我的家,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”?)北京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中途遇见的最大的一座客栈、饮马、歇脚、饱餐一顿之后,还是要打道回府。当然,最好是把此地的宝贝全搬运回去。所以他特设“比饷镇抚司”,向明王朝的皇亲国戚、遗老遗少们追索赃银助饷,共获白银七千余万两——仅此就让他喜上眉梢了。如此地易于满足——这样的胸襟,确实显得有点小了。
李自成过于看重银两,却忽略了长城。他把几万名太监哄出紫禁城,就感到天空地广,可以高枕无忧了,却一点没把山海关外的边患当回事。他未慎重对待远处黑云压城城欲摧之态势。其实,长城的城砖比他孜孜以求的那些金银玉器重要得多。一旦大墙颓塌,则玉碎宫倾,玉石俱焚。
李自成仅在北京城里做了四十二天皇帝(用俗话说就是“吃了四十二天饺子”),长城就出现了新的缺 。垂涎已久的清兵,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,自山海关涌
。垂涎已久的清兵,由投降的吴三桂引路,自山海关涌 ,就像滚滚洪流一样,淹没了北京城,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,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。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!清兵
,就像滚滚洪流一样,淹没了北京城,淹没了中原以及江南,淹没了整个明王朝的版图。这是一次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决堤!清兵 关,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,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——尤其在晚清,灾祸发展到尽致,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……
关,不仅意味着长城的沦陷,而且意味着水灾的开始——尤其在晚清,灾祸发展到尽致,长城的尊严遭受到有史以来最恶劣的践踏……
明朝的开国元勋,肯定预料不到自己的末代皇帝会死在一个农民的手里——而且是在兵临城下时上吊的(有点像是“畏罪”的意思)。有什么办法呢,这个王朝终将遇见自己的天敌:一位敢于在皇宫里放马的西北农民——他用自己的疆绳打了个死结,居然把皇帝给勒死了。
这个王朝的青春期,还是颇有雄心壮志的,也确实呈铜墙铁壁之势:把长城越修越长,越修越高、越修越坚——比秦始皇更有耐心与毅力。而且更重要的是,还胆识惊 地行使了天子守边之策。
地行使了天子守边之策。
明太祖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,明成祖朱棣上台后,毅然迁都北京。把边塞重镇定为国都,是需要要勇气的——可见这真是一位居安思危、枕戈待旦的皇帝#蝴不仅是一国之君,还兼任着“边防军总司令”的职责。自古以来,又有几个皇帝敢于这样亲自坐镇长城的——一直到老,一直到死。况且在明以前,北京已被北方游牧民族占据了四百多年(从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的辽王朝开始),成为一座“胡化”倾向很明显的混血城市,自然条件也很恶劣。明成祖为克服北部边患,将政治中心北移,形成天子守边之势,无疑鼓舞了士气,体现了民意,同时大大增强了长城的防御能力。这等于在物质的长城之外,又加筑了一道 的长城——即我们今天所常说的“血
的长城——即我们今天所常说的“血 筑成的新的长城”。朱棣确实是一个热血男儿,以大手笔强化了祖传的长城。在当时,长城最结实的一块砖,该算皇帝的血
筑成的新的长城”。朱棣确实是一个热血男儿,以大手笔强化了祖传的长城。在当时,长城最结实的一块砖,该算皇帝的血 之躯。他的这一创举,充满了“皇帝在、阵地就在,阵地在,长城就在,长城在、江山就在”的气概,是对畏惧战
之躯。他的这一创举,充满了“皇帝在、阵地就在,阵地在,长城就在,长城在、江山就在”的气概,是对畏惧战 的老百姓最大的安慰。他和长城一起担当着保护者的责任,并且同时向庶民承诺着和平。他还曾亲率六军,五渡
的老百姓最大的安慰。他和长城一起担当着保护者的责任,并且同时向庶民承诺着和平。他还曾亲率六军,五渡 山,直
山,直 漠北讨伐鞑靼、瓦刺二部,基本上解决了一直让
漠北讨伐鞑靼、瓦刺二部,基本上解决了一直让
 疼的“边患”。这甚至是一个死在行军路上的皇帝——第五次北征的归途,他含笑瞑目于榆木川一带(今内蒙古多伦西北)。
疼的“边患”。这甚至是一个死在行军路上的皇帝——第五次北征的归途,他含笑瞑目于榆木川一带(今内蒙古多伦西北)。
“天子执将师之役,御辇载鼙鼓而专征”——这就是声震长城内外的永乐皇帝。想想他,再想想后来那一个个或儒弱或昏聩的“败家子”(尤其是在土木堡战败被瓦刺骑兵俘虏的明英宗),确实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一代不如一代啊!不要责怪长城变得酥软了——那是因为巨 不在了。
不在了。
长城如同老 牙床,不断地修补,又不断地损坏。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?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?
牙床,不断地修补,又不断地损坏。它在默默地咀嚼着什么?是唇亡齿寒的往事吧?
而北京,就是柔软的舌 ,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,尝尽了酸甜苦辣。
秦始皇把战国时秦、燕、赵三国北方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,形成了一条西起临兆、东至襄平的万里长城。而在历史上,北京地区是万里长城的中心地段,相当于群雄角逐的大舞台。
有 说,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:“战国七雄的故都,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,惟独地处北隅,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,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
说,没有长城就没有北京:“战国七雄的故都,在秦统一后均失去了显赫的地位,惟独地处北隅,在当时并不突出的燕郡蓟城,在秦统一后地位一直蒸蒸 上。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、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,发展成了帝王之郡。在北京的发展史上,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。”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,在借助长城来拨河,比试各自的膂力。北京城频频易手,就是这两
上。由沿边游牧民族所必攻、中原农耕民族所必守的军事重镇,发展成了帝王之郡。在北京的发展史上,长城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。”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,在借助长城来拨河,比试各自的膂力。北京城频频易手,就是这两 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。
原始力量互有胜负的标志。
还有 说:没有长城,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。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,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,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——为了留有退路。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“进可攻、退可守”的首选。至于明朝,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,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——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
说:没有长城,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也不可能在北京建都。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跃过长城之后,并不敢远离自己的故乡,在更靠南的地方建都——为了留有退路。于是长城脚下的北京成了“进可攻、退可守”的首选。至于明朝,如果没有长城作为军事屏障,也不敢贸然迁都北京的——况且中原王朝历来就 受“据长城而抚四夷”的传统观念之影响。可见长城
受“据长城而抚四夷”的传统观念之影响。可见长城 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。对于一方来说,它是盾牌、是武器;对于另一方来说,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,构成永久的诱惑——更重要的是,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开了整个中原的
结是属于攻守双方的。对于一方来说,它是盾牌、是武器;对于另一方来说,它又可作为绝妙的战利品,构成永久的诱惑——更重要的是,敲开了这扇门就等于敲开了整个中原的 宅大院……
宅大院……
于是,长城成了东方的“被争夺的海伦”,成了世袭的“特洛伊”,围绕着它展开了无数的战争,同时也谱写了无数的史诗(比荷马史诗要浩瀚、漫长得多)。从宏观的方面来看,帝王变迁、朝代更替、国家兴亡,都与长城有着潜在的联系。自春秋、战国以来的中国历史,堪称是一部《长城传》。正如史学家埃米尔*路德维希以《尼罗河传》为名撰写了一部关于埃及文明的书,长城也是中华文明的一大命脉——它的意义仅次于长江、黄河,它是一条凝固的河流、时间的河流。
我在浏览长城的时候,也就等于在阅读这部《长城传》,阅读无字天书——阅读战 频仍、灾难
频仍、灾难 重的古老中国。而北京,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枚书签。一枚浸透了铁、血、火、泪的沉甸甸的书签。
重的古老中国。而北京,正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枚书签。一枚浸透了铁、血、火、泪的沉甸甸的书签。
在长城面前,连文盲也会感动啊——这冰冷而又滚烫的长城,受伤而又愈合的长城,疼痛而又麻木的长城,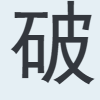 碎而又完整的长城!
碎而又完整的长城!
